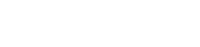龙娶莹从秀竹苑跳窗潜逃那会儿,心里就跟明镜似的。王褚飞那狗鼻子,骆方舟的天罗地网,她这残腿能跑多久?迟早得被逮回去。她龙娶莹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一边在河里扑腾,一边就摸出了怀里早就备好的“护身符”——一封写得声情并茂、字字泣血的检举信。
信里,她把“私自出宫”、“勾结(划掉)协助调查”的黑锅,结结实实、滴水不漏地全扣在了陵酒宴那愣头青头上。尤其重点描述了陵酒宴如何“蛊惑”鹿祁君,如何“利用职权”强行将她带出,字里行间暗示这就是广誉王对王上处置董仲甫一事(当年她爹可没少在背后推波助澜坑她)的蓄意报复。“哼,父债女偿,天经地义!”?她当时写得那叫一个痛快,就指望这封信能在骆方舟盛怒之下,当个稍微有点分量的筹码,换条活路。
可她千算万算,没算到陵酒宴找到她的速度这么快。更没算到,这丫头片子居然趁她昏迷(或是睡着)时,搜了她的身!
彼时,陵酒宴捏着那封墨迹未干的信,手指都在发抖,脸色白得跟纸一样。她看着蜷缩在破庙角落里、浑身湿透狼狈不堪的龙娶莹,只觉得一股寒气从心底冒上来。她以为自己是忍辱负重,借助“工具”破案,却没想到这“工具”转头就能把她卖得干干净净,还要踩上几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人心……竟能险恶至此……”?陵酒宴喃喃自语,眼中最后一点对龙娶莹的、混杂着轻视与利用的复杂情绪,彻底冷了下来。她沉默地将信纸揉成一团,就着摇曳的火堆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
她没有当场揭穿龙娶莹,也没有抓她回去。反而……放走了她。只是,从那一刻起,陵酒宴就像一道沉默的影子,远远地缀在了龙娶莹身后。她要借龙娶莹这条嗅觉敏锐的“疯狗”,找到真正的功劳——盘龙寺的秘密。她要凭自己的本事,拿下这份功绩,让骆方舟,让所有人,都看看她陵酒宴并非只能依靠父辈荫庇!
果然,她跟着龙娶莹找到了大佛后的惊天秘密。甚至,在她和鹿祁君进入佛像区域前,她就凭借之前调查的线索,发现了一条更直接通往寺庙正殿、可能靠近核心区域的路径。当鹿祁君坚持要带龙娶莹回去从长计议时,她看到了那个即将被碾碎的婴儿,也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此刻离开,下次未必还能找到这里,而发现这秘密的首功,很可能因为鹿祁君的证词,落在龙娶莹头上(毕竟是她最先找到入口和姬容)。但如果在混乱中,由她陵酒宴“救下”关键证人(婴儿),并和鹿祁君一同“浴血奋战”后出去报信,那这泼天的功劳,就是她和鹿祁君的!
于是,她“冲动”地站了出来,主动暴露。她算计好了开头,却没算准鹿祁君的反应——他明明知道有近路,明明可以和她一起更快撤离,为何要折返回去救那个屡次背叛、无耻之尤的龙娶莹?甚至不惜自残身体拖延时间?这根本没必要为龙娶莹的逃跑创造时间啊!她想不通。
而她更想不通的是姬容。他盘踞多年,拥有如此多的狂热信徒,为何不拼死一搏,反而选择炸山同归于尽?龙娶莹后来咂摸出味儿了:第一,姬容这变态,目标明确,就是要当时推翻他王朝的几个核心人物——骆方舟、鹿祁君,还有她这个“废王”一起死。第二,他知道渡茶的毒性,只要宫里那些喝了茶的贵族(包括可能中招的骆方舟)毒发,目的也算达成了一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一个双腿齐根断掉的残废,难道还能坐着轮椅挥刀砍杀吗?他手下核心信徒也多是残疾,这副模样去“复国”,他自己都觉得丢人现眼到了极点!与其出去被人像看猴子一样围观、嘲笑,不如拉着所有知情者和仇敌,一起在轰轰烈烈中化为灰烬,还能保留最后一丝“悲壮”的假象。
视线转回压抑的皇宫。
龙娶莹肩头上那个被自己烫平又崩裂、差点要了她半条命的伤口,在裴知?几贴价值千金的灵药下,总算勉强愈合,只留下一个狰狞扭曲的深红色疤痕,趴在她小麦色的皮肤上,像个诡异的烙印。
她此刻正跪在骆方舟寝殿外的汉白玉石阶上,烈日灼心。眼睛却死死盯着不远处鹿祁君养伤的偏殿门口。看着御医进出,看着下人端出一盆盆被血染红的水,她的心就跟放在油锅里煎一样。
“妈的,鹿祁君你小子可千万别死啊……你死了,骆方舟还不得把我剁成肉酱包饺子……”?她嘴里喃喃自语,冷汗顺着额角往下淌。
一片阴影笼罩下来,带着淡淡的药草清苦气。裴知?不知何时站在了她身边,撑着一把素色油纸伞,为她挡去了毒辣的日头。
“阿主在担心什么?”他声音平和,听不出情绪。
龙娶莹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虽然低着头没人看见):“废话!我怕鹿祁君真嗝屁了,那我可就真玩完了!”
裴知?微微俯身,声音低得只有两人能听见:“就这些吗?”
龙娶莹噎了一下,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压低声音,带着点讨好和急切:“还……还有……裴仙人,裴大哥!你……你能不能帮我算算,骆方舟这次……到底会不会宰了我?”她仰起脸,试图从那张永远云淡风轻的脸上找到一丝暗示。
裴知?垂眸看着她,眼神里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怜悯,或者说,是看穿她所有小心思的嘲讽。“阿主,我只算到了你是‘人’。是人,便始终有两份情感在互搏。您的自私自利是真,但那点微末的情义,虽少得像沙漠里的水,却也是真实存在的。您无法做那无情无欲的神,更没办法做那彻头彻尾、毫无挂碍的鬼。”他顿了顿,看向鹿祁君宫殿的方向,“鹿祁君这次伤得极重,王上那边……”
龙娶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王上已经容忍您很多次了。”裴知?的声音依旧平淡,却像重锤敲在她心上,“这一次,他似乎连惩罚您,都懒得费心了。”
“懒得费心?!”?龙娶莹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颓唐地塌下了腰,像只被抽了骨头的癞皮狗。她烦躁地用手抓着早已凌乱的头发,“你就不能给我指条明路吗?!我又不是故意害他伤成那样的!我当时……我当时也是没办法啊!”
裴知?轻轻摇头,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可您早就把人伤透了,不是吗?”
“我不管!”?龙娶莹彻底豁出去了,也顾不得什么形象,猛地扑过去,一把抱住裴知?的大腿,“我求你!我求求你还不行吗!你不是能神机妙算吗?你给我像个办法!我真的不想被骆方舟五马分尸!不想被做成人彘啊!”?她哭嚎着,眼泪鼻涕差点蹭到裴知?雪白的衣袍上。
裴知?身体微微一僵,似乎极力忍耐着把她踢开的冲动,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在下不是说了吗?主动……去道歉。”
龙娶莹抬起头,脸上糊得一塌糊涂,眼神里全是茫然:“道……道歉?就这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龙娶莹在王褚飞那冰冷得能冻死人的目光注视下,一步三挪,扭扭捏捏地蹭进了骆方舟灯火通明的寝殿。
骆方舟正坐在御案后,批阅着关于清剿前朝余孽的后续奏章,头都没抬一下,仿佛她只是一团空气。
“那个……王上……”?龙娶莹捏着嗓子,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可怜一点。
骆方舟置若罔闻,朱笔在奏折上划过的声音清晰可闻。
“你……你理我一下嘛……”?她带着哭腔,往前蹭了几步。
骆方舟终于放下了笔,却依旧没看她,声音平静得可怕:“本王已经遵照你想要的‘帝王’身份,处理完了最后的宣告。毒酒,还是白绫,你自己选一条。”
噗通!
龙娶莹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声音发颤:“求求你!行行好……饶我这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回去吧。”骆方舟重新拿起一份奏折,语气淡漠得像在打发一只苍蝇,“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本王对将死之人,已经没兴趣了。”
龙娶莹真的没辙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裴知?那句“道歉”。她连滚带爬地冲到御案前,双手捧起旁边装饰用的一根镶玉皮鞭,高高举过头顶,声音带着绝望的哭喊:“求你罚我吧!怎么罚我都行!把我揍个半死!抽得皮开肉绽都可以!只要别杀我!”
骆方舟连眼皮都懒得抬,彻底无视了她。
龙娶莹心一横,把最后那点羞耻心也扔到了九霄云外。她猛地转身,扑过去紧紧抱住骆方舟的大腿,脸贴在他冰凉的蟒袍上,语无伦次地哀求:“你让我生孩子也可以!我不偷偷喝避子汤了!我保证!你让我怀你的孩子都可以!求你了……别杀我……我不想死……”
骆方舟终于有了反应。
他合上手中的奏折,缓缓地,将目光落在了她涕泪交加的脸上。那眼神,像是审视一件肮脏的、却又有点新奇玩意的物品。
“你?”他嘴角勾起一抹极尽讥诮的弧度,“想做母亲?”他的手指,冰凉而有力,捏住她的下巴,迫使她抬起脸,“你这身子,被多少人碰过?王褚飞?鹿祁君?还是秀竹苑里那十几个男妓?这般人尽可夫、肮脏不堪的身子,也配……也敢想生下本王的种?”
(有反应总比没反应强!)?龙娶莹捕捉到他眼底一丝微不可察的波动,立刻顺着杆子往上爬,抱紧他的腿,急声道:“你把我锁起来!囚禁起来!就关在你眼皮子底下!干到我怀孕为止!那……那孩子不就能确保是你的了吗?”?为了活命,她什么都能许诺。
骆方舟盯着她,眼神深邃得像寒潭,仿佛要看穿她灵魂深处的谎言与算计。“看来你终于明白,”他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危险的磁性,“这孩子的出生,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你龙娶莹彻底放弃争夺皇位的野心,你的血脉将永远打上他骆方舟的烙印,这个孩子将来或许会成为太子,成为皇帝,而龙娶莹,将彻底沦为他的附属品,被他永远掌控。
(但是怎么可能?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活下去的筹码罢了!)?龙娶莹心里在呐喊,脸上却努力挤出一副顺从甚至带着点卑微渴望的表情,声音细若蚊蚋:“我……我知道……”
骆方舟盯着她看了半晌,忽然抬脚,不算太重,却带着十足的羞辱意味,将她踹倒在地。“龙娶莹啊龙娶莹,”?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语气复杂难辨,“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不过……你这般厚颜无耻,想必也根本不在乎这些吧。”?对他而言,一个流着他血脉的孩子出生,就是最好的保障和枷锁。有了这个孩子,无论她再怎么折腾,都翻不出他的手掌心了。
听到这话,龙娶莹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咕咚”一声落回了肚子里。妈的,终于……暂时死不了了!
然而,她这口气还没喘匀,下一秒,骆方舟就猛地俯身,一把拽住她的前襟,将她整个人粗暴地提了起来,然后“咣当”一声巨响,重重地按在了坚硬的紫檀木御案之上!奏折、笔墨纸砚被撞得散落一地。
“自己把裤子脱了,润滑好。”?他命令道,声音里没有任何情欲,只有冰冷的掌控和即将实施的惩罚。他自己则慢条斯理地解开龙袍的腰带,那早已勃起、青筋虬结的粗长肉棒弹跳而出,硕大的龟头泛着紫红色,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龙娶莹被摔得七荤八素,眼冒金星,闻言不敢怠慢,颤抖着手扯下自己的亵裤,就着之前紧张时分泌的些许湿意,胡乱在腿心那处早已熟悉侵犯、却依旧紧致的肉穴口涂抹了几下。
“自己掰好了!”?骆方舟对于她慢吞吞的动作和那点微不足道的润滑似乎极为不满,语气森寒。
龙娶莹咬着牙,认命地用手分开自己肥白圆润的臀瓣,将中间那朵微微翕动、泛着水光的肉缝暴露在他眼前。她下意识地咬住了散落的衣摆,试图抵御即将到来的冲击。
骆方舟没有任何前戏,扶着自己那根堪比儿臂的狰狞肉棒,对准那微微开合的穴口,腰身猛地一沉,“噗嗤”一声,尽根没入!
“唔啊——!!!”
一股被强行撑裂、贯穿到底的剧痛瞬间席卷了龙娶莹的全身!她感觉自己的阴户像是要被活活撕成两半,子宫都被顶得狠狠一颤,眼前阵阵发黑。“骆方舟……还是……好痛啊……”?她带着哭腔呻吟,身体下意识地想要蜷缩逃离。
“别乱动!”?骆方舟的大手如同铁钳般按住她胡乱扭动的腰背,将她死死固定在冰冷的桌面上,“因为这次得进得深一点,要狠狠插入你这骚狗的宫腔,让你好好记住,谁才是你的主人,谁才能在你这里面留下种!”
“哈啊……可是……真的太深了……”?龙娶莹感觉他那玩意儿简直不像肉棒,倒像是一根烧红的烙铁,每一次顶撞都又深又重,龟头次次都精准地碾过她体内最敏感的褶皱,直捣黄龙般撞击着娇嫩的宫口。之前的侵犯多是快进快出,虽然难受,但好歹适应得快。这次,她感觉每一次深入都像是顶到了胃,让她阵阵干呕,五脏六腑都错了位。
骆方舟似乎对她身体内部的反应产生了点兴趣,粗壮的茎身在她紧致湿滑的甬道里霸道地冲撞,感受着那软肉不自觉地吸附和绞紧。?“哼,你这里面……倒是又软又湿,像张贪吃的小嘴。”?他故意用语言羞辱她,下身撞击的力道却一下重过一下,每一次退出都带出些许糜烂的水声,每一次进入都更深更狠,?“砰!砰!砰!”?结实的小腹撞击在她丰满的臀肉上,发出响亮而羞耻的声音,肥白的臀浪随着他的动作剧烈荡漾。
“啊……慢点……受不住了……真的要坏了……”?龙娶莹徒劳地哀求着,手指死死抠着光滑的桌面,指尖泛白。痛楚和一种被强行开发出的、违背她意志的快感交织在一起,让她的大脑一片混乱。淫水不受控制地汩汩流出,浸润了两人交合处,也弄湿了冰冷的桌面。
这场单方面的、带着惩罚和宣告主权意味的性事,持续了不知多久。直到骆方舟一声低吼,将一股滚烫的精液猛烈地灌入她身体深处,冲击着她敏感脆弱的宫腔。龙娶莹早已像条离水的鱼,除了颤抖和呜咽,再做不出任何反应。
自那晚之后,龙娶莹就被彻底囚禁在了骆方舟寝殿的偏殿里。他不在的时候,一条特制的、内嵌柔软丝绸却依旧冰冷坚硬的贞操带就会锁在她腰间,将她那处饱受蹂躏的私密花园牢牢封锁。龙娶莹看着那玩意儿,只觉得无比讽刺和无奈。
只有在晚上,骆方舟过来“例行公事”,逼她受孕的时候,那贞操带才会被暂时解开。而王褚飞,就像一尊沉默的石像,日夜守在偏殿门口。
有一次,龙娶莹实在被这方寸之地憋疯了,试图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结果下一秒,王褚飞的剑鞘就横在了她面前,冰冷无情。
“我就想去看看鹿祁君死了没有!”?她气得大叫。
王褚飞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仿佛没听见。
压抑和绝望终于爆发了。龙娶莹像头困兽,抓起手边能碰到的一切——花瓶、茶具、摆件,疯狂地砸向墙壁、地面!“噼里啪啦”的碎裂声不绝于耳,瓷片和玻璃碎片四处飞溅!?一块锋利的碎瓷片擦过王褚飞的脸颊,瞬间留下一道血痕,鲜血顺着他的下颌线滑落。
他却依旧面无表情,甚至连眼神都没有丝毫波动,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发疯。
龙娶莹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瘫坐在一片狼藉之中,胸口剧烈起伏,发出绝望的嘶吼:“该死!!!全都该死!!!”
晚上,骆方舟归来,看着满殿狼藉和坐在碎片中、眼神空洞的龙娶莹,什么也没问。只是那双眼睛里,酝酿着比之前更深的风暴。
“看来,是本王对你太宽容了。”
他直接将她拖到床边,用结实的绸带将她四肢分开,呈“大”字型牢牢绑在床柱上。龙娶莹像只待宰的羔羊,徒劳地挣扎着,眼中终于露出了恐惧。
骆方舟解下腰带,那坚韧的牛皮带着破空声,“啪!”?地一下,狠狠抽在她光裸的、肥白而满是旧鞭痕的臀肉上!
“啊!”?龙娶莹痛得惨叫一声,臀上瞬间浮现一道鲜明的红棱。
“以后再敢如此放肆,”?骆方舟的声音冰冷如铁,“本王不介意把你全身的骨头,一根一根,全都敲碎。让你真真正正,变成一滩只能躺在床上的烂肉。”
龙娶莹吓得浑身发抖,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
骆方舟却不再多言,直起身,就着她被捆绑的姿势,粗暴地扯下她的亵裤,将自己早已再次勃起怒张的肉棒,对准那昨晚才被狠狠疼爱过、此刻依旧有些红肿的肉穴,没有任何润滑,直接狠狠地捅了进去!
“呃啊啊——!”?干涩的侵入带来撕裂般的痛楚,龙娶莹仰起脖子,发出凄厉的哀鸣。
骆方舟却仿佛听不见,抓住她丰腴的腰肢,开始了一场毫无怜惜、只有纯粹征服与发泄的挞伐。每一次撞击都又深又重,囊袋拍打在她臀缝,发出淫靡的声响。粗长的肉棒在她紧窒的甬道里横冲直撞,摩擦着娇嫩的媚肉,带出更多的疼痛和被迫分泌的润滑。
他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彻底碾碎她所有的反抗意志,将她钉死在这张象征着屈辱和控制的龙床之上。
殿内只剩下肉体碰撞的啪啪声、铁链摇晃的细碎声响,以及龙娶莹那断断续续、痛苦而压抑的呻吟与呜咽。
信里,她把“私自出宫”、“勾结(划掉)协助调查”的黑锅,结结实实、滴水不漏地全扣在了陵酒宴那愣头青头上。尤其重点描述了陵酒宴如何“蛊惑”鹿祁君,如何“利用职权”强行将她带出,字里行间暗示这就是广誉王对王上处置董仲甫一事(当年她爹可没少在背后推波助澜坑她)的蓄意报复。“哼,父债女偿,天经地义!”?她当时写得那叫一个痛快,就指望这封信能在骆方舟盛怒之下,当个稍微有点分量的筹码,换条活路。
可她千算万算,没算到陵酒宴找到她的速度这么快。更没算到,这丫头片子居然趁她昏迷(或是睡着)时,搜了她的身!
彼时,陵酒宴捏着那封墨迹未干的信,手指都在发抖,脸色白得跟纸一样。她看着蜷缩在破庙角落里、浑身湿透狼狈不堪的龙娶莹,只觉得一股寒气从心底冒上来。她以为自己是忍辱负重,借助“工具”破案,却没想到这“工具”转头就能把她卖得干干净净,还要踩上几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人心……竟能险恶至此……”?陵酒宴喃喃自语,眼中最后一点对龙娶莹的、混杂着轻视与利用的复杂情绪,彻底冷了下来。她沉默地将信纸揉成一团,就着摇曳的火堆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
她没有当场揭穿龙娶莹,也没有抓她回去。反而……放走了她。只是,从那一刻起,陵酒宴就像一道沉默的影子,远远地缀在了龙娶莹身后。她要借龙娶莹这条嗅觉敏锐的“疯狗”,找到真正的功劳——盘龙寺的秘密。她要凭自己的本事,拿下这份功绩,让骆方舟,让所有人,都看看她陵酒宴并非只能依靠父辈荫庇!
果然,她跟着龙娶莹找到了大佛后的惊天秘密。甚至,在她和鹿祁君进入佛像区域前,她就凭借之前调查的线索,发现了一条更直接通往寺庙正殿、可能靠近核心区域的路径。当鹿祁君坚持要带龙娶莹回去从长计议时,她看到了那个即将被碾碎的婴儿,也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此刻离开,下次未必还能找到这里,而发现这秘密的首功,很可能因为鹿祁君的证词,落在龙娶莹头上(毕竟是她最先找到入口和姬容)。但如果在混乱中,由她陵酒宴“救下”关键证人(婴儿),并和鹿祁君一同“浴血奋战”后出去报信,那这泼天的功劳,就是她和鹿祁君的!
于是,她“冲动”地站了出来,主动暴露。她算计好了开头,却没算准鹿祁君的反应——他明明知道有近路,明明可以和她一起更快撤离,为何要折返回去救那个屡次背叛、无耻之尤的龙娶莹?甚至不惜自残身体拖延时间?这根本没必要为龙娶莹的逃跑创造时间啊!她想不通。
而她更想不通的是姬容。他盘踞多年,拥有如此多的狂热信徒,为何不拼死一搏,反而选择炸山同归于尽?龙娶莹后来咂摸出味儿了:第一,姬容这变态,目标明确,就是要当时推翻他王朝的几个核心人物——骆方舟、鹿祁君,还有她这个“废王”一起死。第二,他知道渡茶的毒性,只要宫里那些喝了茶的贵族(包括可能中招的骆方舟)毒发,目的也算达成了一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一个双腿齐根断掉的残废,难道还能坐着轮椅挥刀砍杀吗?他手下核心信徒也多是残疾,这副模样去“复国”,他自己都觉得丢人现眼到了极点!与其出去被人像看猴子一样围观、嘲笑,不如拉着所有知情者和仇敌,一起在轰轰烈烈中化为灰烬,还能保留最后一丝“悲壮”的假象。
视线转回压抑的皇宫。
龙娶莹肩头上那个被自己烫平又崩裂、差点要了她半条命的伤口,在裴知?几贴价值千金的灵药下,总算勉强愈合,只留下一个狰狞扭曲的深红色疤痕,趴在她小麦色的皮肤上,像个诡异的烙印。
她此刻正跪在骆方舟寝殿外的汉白玉石阶上,烈日灼心。眼睛却死死盯着不远处鹿祁君养伤的偏殿门口。看着御医进出,看着下人端出一盆盆被血染红的水,她的心就跟放在油锅里煎一样。
“妈的,鹿祁君你小子可千万别死啊……你死了,骆方舟还不得把我剁成肉酱包饺子……”?她嘴里喃喃自语,冷汗顺着额角往下淌。
一片阴影笼罩下来,带着淡淡的药草清苦气。裴知?不知何时站在了她身边,撑着一把素色油纸伞,为她挡去了毒辣的日头。
“阿主在担心什么?”他声音平和,听不出情绪。
龙娶莹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虽然低着头没人看见):“废话!我怕鹿祁君真嗝屁了,那我可就真玩完了!”
裴知?微微俯身,声音低得只有两人能听见:“就这些吗?”
龙娶莹噎了一下,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压低声音,带着点讨好和急切:“还……还有……裴仙人,裴大哥!你……你能不能帮我算算,骆方舟这次……到底会不会宰了我?”她仰起脸,试图从那张永远云淡风轻的脸上找到一丝暗示。
裴知?垂眸看着她,眼神里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怜悯,或者说,是看穿她所有小心思的嘲讽。“阿主,我只算到了你是‘人’。是人,便始终有两份情感在互搏。您的自私自利是真,但那点微末的情义,虽少得像沙漠里的水,却也是真实存在的。您无法做那无情无欲的神,更没办法做那彻头彻尾、毫无挂碍的鬼。”他顿了顿,看向鹿祁君宫殿的方向,“鹿祁君这次伤得极重,王上那边……”
龙娶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王上已经容忍您很多次了。”裴知?的声音依旧平淡,却像重锤敲在她心上,“这一次,他似乎连惩罚您,都懒得费心了。”
“懒得费心?!”?龙娶莹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颓唐地塌下了腰,像只被抽了骨头的癞皮狗。她烦躁地用手抓着早已凌乱的头发,“你就不能给我指条明路吗?!我又不是故意害他伤成那样的!我当时……我当时也是没办法啊!”
裴知?轻轻摇头,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可您早就把人伤透了,不是吗?”
“我不管!”?龙娶莹彻底豁出去了,也顾不得什么形象,猛地扑过去,一把抱住裴知?的大腿,“我求你!我求求你还不行吗!你不是能神机妙算吗?你给我像个办法!我真的不想被骆方舟五马分尸!不想被做成人彘啊!”?她哭嚎着,眼泪鼻涕差点蹭到裴知?雪白的衣袍上。
裴知?身体微微一僵,似乎极力忍耐着把她踢开的冲动,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在下不是说了吗?主动……去道歉。”
龙娶莹抬起头,脸上糊得一塌糊涂,眼神里全是茫然:“道……道歉?就这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龙娶莹在王褚飞那冰冷得能冻死人的目光注视下,一步三挪,扭扭捏捏地蹭进了骆方舟灯火通明的寝殿。
骆方舟正坐在御案后,批阅着关于清剿前朝余孽的后续奏章,头都没抬一下,仿佛她只是一团空气。
“那个……王上……”?龙娶莹捏着嗓子,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可怜一点。
骆方舟置若罔闻,朱笔在奏折上划过的声音清晰可闻。
“你……你理我一下嘛……”?她带着哭腔,往前蹭了几步。
骆方舟终于放下了笔,却依旧没看她,声音平静得可怕:“本王已经遵照你想要的‘帝王’身份,处理完了最后的宣告。毒酒,还是白绫,你自己选一条。”
噗通!
龙娶莹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声音发颤:“求求你!行行好……饶我这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回去吧。”骆方舟重新拿起一份奏折,语气淡漠得像在打发一只苍蝇,“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本王对将死之人,已经没兴趣了。”
龙娶莹真的没辙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裴知?那句“道歉”。她连滚带爬地冲到御案前,双手捧起旁边装饰用的一根镶玉皮鞭,高高举过头顶,声音带着绝望的哭喊:“求你罚我吧!怎么罚我都行!把我揍个半死!抽得皮开肉绽都可以!只要别杀我!”
骆方舟连眼皮都懒得抬,彻底无视了她。
龙娶莹心一横,把最后那点羞耻心也扔到了九霄云外。她猛地转身,扑过去紧紧抱住骆方舟的大腿,脸贴在他冰凉的蟒袍上,语无伦次地哀求:“你让我生孩子也可以!我不偷偷喝避子汤了!我保证!你让我怀你的孩子都可以!求你了……别杀我……我不想死……”
骆方舟终于有了反应。
他合上手中的奏折,缓缓地,将目光落在了她涕泪交加的脸上。那眼神,像是审视一件肮脏的、却又有点新奇玩意的物品。
“你?”他嘴角勾起一抹极尽讥诮的弧度,“想做母亲?”他的手指,冰凉而有力,捏住她的下巴,迫使她抬起脸,“你这身子,被多少人碰过?王褚飞?鹿祁君?还是秀竹苑里那十几个男妓?这般人尽可夫、肮脏不堪的身子,也配……也敢想生下本王的种?”
(有反应总比没反应强!)?龙娶莹捕捉到他眼底一丝微不可察的波动,立刻顺着杆子往上爬,抱紧他的腿,急声道:“你把我锁起来!囚禁起来!就关在你眼皮子底下!干到我怀孕为止!那……那孩子不就能确保是你的了吗?”?为了活命,她什么都能许诺。
骆方舟盯着她,眼神深邃得像寒潭,仿佛要看穿她灵魂深处的谎言与算计。“看来你终于明白,”他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危险的磁性,“这孩子的出生,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你龙娶莹彻底放弃争夺皇位的野心,你的血脉将永远打上他骆方舟的烙印,这个孩子将来或许会成为太子,成为皇帝,而龙娶莹,将彻底沦为他的附属品,被他永远掌控。
(但是怎么可能?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活下去的筹码罢了!)?龙娶莹心里在呐喊,脸上却努力挤出一副顺从甚至带着点卑微渴望的表情,声音细若蚊蚋:“我……我知道……”
骆方舟盯着她看了半晌,忽然抬脚,不算太重,却带着十足的羞辱意味,将她踹倒在地。“龙娶莹啊龙娶莹,”?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语气复杂难辨,“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不过……你这般厚颜无耻,想必也根本不在乎这些吧。”?对他而言,一个流着他血脉的孩子出生,就是最好的保障和枷锁。有了这个孩子,无论她再怎么折腾,都翻不出他的手掌心了。
听到这话,龙娶莹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咕咚”一声落回了肚子里。妈的,终于……暂时死不了了!
然而,她这口气还没喘匀,下一秒,骆方舟就猛地俯身,一把拽住她的前襟,将她整个人粗暴地提了起来,然后“咣当”一声巨响,重重地按在了坚硬的紫檀木御案之上!奏折、笔墨纸砚被撞得散落一地。
“自己把裤子脱了,润滑好。”?他命令道,声音里没有任何情欲,只有冰冷的掌控和即将实施的惩罚。他自己则慢条斯理地解开龙袍的腰带,那早已勃起、青筋虬结的粗长肉棒弹跳而出,硕大的龟头泛着紫红色,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龙娶莹被摔得七荤八素,眼冒金星,闻言不敢怠慢,颤抖着手扯下自己的亵裤,就着之前紧张时分泌的些许湿意,胡乱在腿心那处早已熟悉侵犯、却依旧紧致的肉穴口涂抹了几下。
“自己掰好了!”?骆方舟对于她慢吞吞的动作和那点微不足道的润滑似乎极为不满,语气森寒。
龙娶莹咬着牙,认命地用手分开自己肥白圆润的臀瓣,将中间那朵微微翕动、泛着水光的肉缝暴露在他眼前。她下意识地咬住了散落的衣摆,试图抵御即将到来的冲击。
骆方舟没有任何前戏,扶着自己那根堪比儿臂的狰狞肉棒,对准那微微开合的穴口,腰身猛地一沉,“噗嗤”一声,尽根没入!
“唔啊——!!!”
一股被强行撑裂、贯穿到底的剧痛瞬间席卷了龙娶莹的全身!她感觉自己的阴户像是要被活活撕成两半,子宫都被顶得狠狠一颤,眼前阵阵发黑。“骆方舟……还是……好痛啊……”?她带着哭腔呻吟,身体下意识地想要蜷缩逃离。
“别乱动!”?骆方舟的大手如同铁钳般按住她胡乱扭动的腰背,将她死死固定在冰冷的桌面上,“因为这次得进得深一点,要狠狠插入你这骚狗的宫腔,让你好好记住,谁才是你的主人,谁才能在你这里面留下种!”
“哈啊……可是……真的太深了……”?龙娶莹感觉他那玩意儿简直不像肉棒,倒像是一根烧红的烙铁,每一次顶撞都又深又重,龟头次次都精准地碾过她体内最敏感的褶皱,直捣黄龙般撞击着娇嫩的宫口。之前的侵犯多是快进快出,虽然难受,但好歹适应得快。这次,她感觉每一次深入都像是顶到了胃,让她阵阵干呕,五脏六腑都错了位。
骆方舟似乎对她身体内部的反应产生了点兴趣,粗壮的茎身在她紧致湿滑的甬道里霸道地冲撞,感受着那软肉不自觉地吸附和绞紧。?“哼,你这里面……倒是又软又湿,像张贪吃的小嘴。”?他故意用语言羞辱她,下身撞击的力道却一下重过一下,每一次退出都带出些许糜烂的水声,每一次进入都更深更狠,?“砰!砰!砰!”?结实的小腹撞击在她丰满的臀肉上,发出响亮而羞耻的声音,肥白的臀浪随着他的动作剧烈荡漾。
“啊……慢点……受不住了……真的要坏了……”?龙娶莹徒劳地哀求着,手指死死抠着光滑的桌面,指尖泛白。痛楚和一种被强行开发出的、违背她意志的快感交织在一起,让她的大脑一片混乱。淫水不受控制地汩汩流出,浸润了两人交合处,也弄湿了冰冷的桌面。
这场单方面的、带着惩罚和宣告主权意味的性事,持续了不知多久。直到骆方舟一声低吼,将一股滚烫的精液猛烈地灌入她身体深处,冲击着她敏感脆弱的宫腔。龙娶莹早已像条离水的鱼,除了颤抖和呜咽,再做不出任何反应。
自那晚之后,龙娶莹就被彻底囚禁在了骆方舟寝殿的偏殿里。他不在的时候,一条特制的、内嵌柔软丝绸却依旧冰冷坚硬的贞操带就会锁在她腰间,将她那处饱受蹂躏的私密花园牢牢封锁。龙娶莹看着那玩意儿,只觉得无比讽刺和无奈。
只有在晚上,骆方舟过来“例行公事”,逼她受孕的时候,那贞操带才会被暂时解开。而王褚飞,就像一尊沉默的石像,日夜守在偏殿门口。
有一次,龙娶莹实在被这方寸之地憋疯了,试图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结果下一秒,王褚飞的剑鞘就横在了她面前,冰冷无情。
“我就想去看看鹿祁君死了没有!”?她气得大叫。
王褚飞连眼皮都没动一下,仿佛没听见。
压抑和绝望终于爆发了。龙娶莹像头困兽,抓起手边能碰到的一切——花瓶、茶具、摆件,疯狂地砸向墙壁、地面!“噼里啪啦”的碎裂声不绝于耳,瓷片和玻璃碎片四处飞溅!?一块锋利的碎瓷片擦过王褚飞的脸颊,瞬间留下一道血痕,鲜血顺着他的下颌线滑落。
他却依旧面无表情,甚至连眼神都没有丝毫波动,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发疯。
龙娶莹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瘫坐在一片狼藉之中,胸口剧烈起伏,发出绝望的嘶吼:“该死!!!全都该死!!!”
晚上,骆方舟归来,看着满殿狼藉和坐在碎片中、眼神空洞的龙娶莹,什么也没问。只是那双眼睛里,酝酿着比之前更深的风暴。
“看来,是本王对你太宽容了。”
他直接将她拖到床边,用结实的绸带将她四肢分开,呈“大”字型牢牢绑在床柱上。龙娶莹像只待宰的羔羊,徒劳地挣扎着,眼中终于露出了恐惧。
骆方舟解下腰带,那坚韧的牛皮带着破空声,“啪!”?地一下,狠狠抽在她光裸的、肥白而满是旧鞭痕的臀肉上!
“啊!”?龙娶莹痛得惨叫一声,臀上瞬间浮现一道鲜明的红棱。
“以后再敢如此放肆,”?骆方舟的声音冰冷如铁,“本王不介意把你全身的骨头,一根一根,全都敲碎。让你真真正正,变成一滩只能躺在床上的烂肉。”
龙娶莹吓得浑身发抖,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
骆方舟却不再多言,直起身,就着她被捆绑的姿势,粗暴地扯下她的亵裤,将自己早已再次勃起怒张的肉棒,对准那昨晚才被狠狠疼爱过、此刻依旧有些红肿的肉穴,没有任何润滑,直接狠狠地捅了进去!
“呃啊啊——!”?干涩的侵入带来撕裂般的痛楚,龙娶莹仰起脖子,发出凄厉的哀鸣。
骆方舟却仿佛听不见,抓住她丰腴的腰肢,开始了一场毫无怜惜、只有纯粹征服与发泄的挞伐。每一次撞击都又深又重,囊袋拍打在她臀缝,发出淫靡的声响。粗长的肉棒在她紧窒的甬道里横冲直撞,摩擦着娇嫩的媚肉,带出更多的疼痛和被迫分泌的润滑。
他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彻底碾碎她所有的反抗意志,将她钉死在这张象征着屈辱和控制的龙床之上。
殿内只剩下肉体碰撞的啪啪声、铁链摇晃的细碎声响,以及龙娶莹那断断续续、痛苦而压抑的呻吟与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