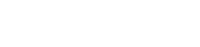晨光刺破薄雾时,穹顶竞技馆已座无虚席。
赌盘开盘价一路飙升,因为决赛对阵表上那两个名字。
天城黎音(摩纳哥) vs 京极真(日本)
没人料到潘克拉辛能走到这一步。
伊什塔尔站在选手通道阴影里,指尖抚过颈侧。只是一晚,昨夜匕首擦过的伤痕就只剩下了浅浅白痕。
她吞下最后一口红子给的魔药,苦涩中带着一丝玫瑰的香气。
“十二小时内不会失控。”红子当时说,“但别指望它让你变成石头。”
她深吸一口气,走向擂台。
京极真正站在中央,白色武道服一尘不染,双脚微开,重心沉于丹田,双手自然垂落,是标准的极真空手道“自然体”起式。他没看观众,也没看裁判,目光只落在她脚步落点上。
裁判示意开始。
伊什塔尔没有废话。
她左脚蹬地,整个人如箭突进,右腿低扫直取他支撑腿膝窝。这是潘克拉辛最凶的开场,意在破坏平衡,继而抱腿摔投。
但京极真没后退。他左脚内扣,小腿肌肉绷紧如铁,硬生生扛下这一扫。
下一秒,他右拳如炮弹轰出。直线正拳,极真空手道的标志性技法,快得几乎撕裂空气。
伊什塔尔偏头避过,拳风擦过耳际,带起一阵刺痛。
她顺势切入内围,左手擒他右腕,右手锁他肘关节,欲借力掀翻。可京极真猛地沉肩,肘部如钢柱般纹丝不动。
他左腿闪电般踢出。中段前踢,直奔她肋下。
她松手后撤,却仍被踢中腰侧,闷哼一声。
掌心无意擦过他小臂。刹那间,一股热流从脊椎窜上后颈。
心跳骤快,指尖发麻。
但她咬住舌尖,压下那阵灼烧感。
魔药生效了,燥热被一层薄纱隔住,不至于失控。
确定魔药的效力,她不再追求一击必杀,改用游走战术,利用潘克拉辛的灵活性绕场周旋。
突然,她假意左扑,诱他出拳。
京极真果然右拳递出。
她瞬间变向,从他右侧切入,右膝猛撞其腰腹。
他闷哼,却未弯腰。
极真空手道讲究“受击如山”,越是痛,越要稳。
他左手抓住她衣襟,不是摔,而是猛地一拉,同时右腿横扫。
回旋踢!
风声呼啸,若被踢实,肋骨必断。
看来京极真确实认真起来了。
伊什塔尔仰身后折,脊背几乎贴地,发丝被踢风削断几缕。
起身瞬间,她欺身而上,双臂锁他咽喉。
全场哗然。
京极真脖颈青筋暴起,呼吸受阻,却未慌乱。
他双手并未去掰她手臂,而是猛地屈膝上顶,让伊什塔尔被迫松手后跳。
两人喘息交错,汗珠从额角滑落,在地板上砸出深色圆点。
节奏更快了。
她连续三次低扫,逼他不断格挡。然后,她虚晃一腿,突然跃起,右腿如鞭抽向他头部。
京极真抬臂格挡,小臂与她小腿相撞,发出沉闷声响。
两人同时后退半步,手臂都在颤抖。
又一次缠斗中,她的掌心按上他胸口,借力翻身。
热流再度涌上,但这次,她竟察觉到一丝异样。
他的皮肤在发烫。不是因为运动的热,而是像她之前那样,烫得不正常。
她心头一震,动作微滞。
京极真立刻抓住这半秒破绽,左脚踏前,右腿如刀劈下。
极真空手道最强杀招,力量集中于脚,若是用力大些,甚至可碎砖裂石。
她交叉格挡,却被踹得连退五步,肩胛撞上擂台边缘绳索,剧痛钻心。
但她依旧没倒。
咬牙站稳,摆出潘克拉辛的“战龟式”。重心下沉,双臂护肋,只露双眼。
京极真没追击。他站在原地,微微喘息,额角汗珠滚落。他的目光第一次有了波动,是终于遇到对手的热切。
两人再次对冲。
伊什塔尔佯攻左路,实则右腿扫下盘。京极真跃起避让,落地瞬间,左拳直刺她面门。
她偏头,右手擒他手腕,左手锁肘,欲使“海蛇绞”。但就在她贴近的刹那,掌心贴上他汗湿的胸膛。
这一次,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燥热竟然减弱了不少。而京极真却明显一僵,呼吸乱了一拍。
就是现在!
她发力拧转。可京极真竟在失衡瞬间,以不可思议的腰力强行稳住,反手抓住她衣领,借她自身冲势,将她狠狠掼向地面。
不是摔投,是投技中的崩落。极真空手道极少用,但一旦用出,便是终结。
她后背砸地,眼前一黑。
裁判立刻介入。
“胜者——京极真!”
掌声雷动。
伊什塔尔躺在地上,盯着天花板,胸口剧烈起伏。
右手微微发颤,不是因为痛,而是因差那半秒。
如果她再快一点,如果他没在最后关头稳住……
京极真走过来,身上也终于多了不少灰尘和破损递。
“你很强。”他说,“下次,你在第三回合换重心的时候,左膝比右肩更先暴露。你的小习惯在武道场上也会成为破绽。”
说完,他转身离开。
伊什塔尔爬起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只有像他这样观察细致,有足够经验,又真正算得上有天赋的武道巅峰级的选手才会真正抓住她的那一点破绽。如果换一个人,就算是发现了她的破绽,也不会那么轻易让她的‘破绽’成为破绽。
但他指出了她的破绽,这是武者的最高敬意,她收下了。
她摸了摸自己胸口,那里不再灼热,不同于之前,现在一点多余的感觉都没有。她想起他最后那一瞬的僵硬。
他的体温,好像……又升高了?
黄昏,场馆人潮退去。
伊什塔尔没回酒店。她坐在空荡的观众席最后一排,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右肩。虽然她在当隐形人的那些年里早就变得不怕死不怕痛,但京极真侧踹的位置的钝痛感还是让她感觉有些不适,能感觉到他当时到底有多用力。
虽然有些不甘心没有拿到冠军,但更让她感兴趣的是他最后那一瞬间的僵硬。是真的失衡,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风从高窗灌入,带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咸味。她忽然站起身,走向选手通道。
休息区早已清空。京极真的储物柜开着,里面只剩一条用过的毛巾。他的东西应该已经被教练或是同行人带走了,这条毛巾大概是他还没准备离开的时候放在这的。
总不可能是忘记了吧?
她伸手碰了下,布料冰凉,至少一小时前就离开了。
她走出场馆后门,沿着围墙缓步。
武道大会结束后,安保松懈,连便衣都撤了大半。只有清洁工在冲洗擂台血迹。
她本来应该回酒店的,可脚步却转向西侧。
那是他赛后离场的方向。
小巷幽深,堆着废弃的器材箱和折迭椅。她走过一半,忽然停住。
地上有一道拖痕,是身体被拖行时留下的压痕,从巷口延伸至一堆防水布后。
她蹲下,指尖沾了点灰,捻开,上面混着汗渍和一点暗红。
是血?还是擦伤?
她掀开防水布。
京极真正靠墙坐着,头垂在胸前,武道服领口敞开,脸上的红晕透过小麦色的皮肤也能看得十分清晰。他呼吸急促,额角全是冷汗,锁骨处皮肤泛着不正常的潮红。
她蹲下,试探他颈侧脉搏。
又快又乱。
“京极?”她轻唤。
没反应。
她伸手扶他肩膀,想拉他起来。但就在掌心贴上他皮肤的瞬间,那熟悉的燥热感涌上来。
奇怪的是,这次她只觉微温,像夏日余晖的温暖。而他的体温却烫得惊人,仿佛体内烧着一把火。
看来是症状转移了。
她立刻拨通红子的电话。
“喂?”红子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背景有烛火噼啪声。
“我碰到京极真了。”伊什塔尔说,“他晕倒了,体温异常高,但我几乎没感觉。”
电话那头静了一秒。
“哦?”红子轻笑,“看来药起作用了。”
“你的魔药做了什么,居然还有这种妙用。早知道我早用了,也省得我每次碰到他都受这种折磨。”
“不是‘做了什么’,”她慢悠悠地说,“是‘转移了什么’。那东西需要容器,你只是暂时保管。现在它找到更合适的了。”
“另外,我要提醒你一点。你之前遇到他的时候,我好像和你也没那么熟。”
别说熟了,她们甚至不认识。
伊什塔尔感觉有点有趣,但还是继续问她,“更合适是什么意思?”
“他的身体比你更能承受那种热度。”红子顿了顿,声音忽然压低,“红魔女的魔法,从来不会无缘无故选中两个人。”
“所以?”她问。
“所以——”红子拖长音,带着一丝戏谑,“既然他现在动不了……你不好奇,他心跳加速,到底是因为武道,还是别的?”
没等回答,她就挂了。
不是,她这话是何意味?
咬了咬牙,把脑子里的东西都清空,她俯身将他一只手臂搭上自己肩头,另一手托住他腰背,慢慢架起。
他比看起来更重,肌肉紧绷,即便昏迷也不肯彻底放松。
她咬牙撑住,一步步往酒店方向走。
路灯亮起时,她后背已湿透,但胸口不再发烫,反而有种奇异的平静。
回到酒店,她只开了一盏床头灯,暖橙色的光映得房间好像都温馨起来。
窗外伊斯坦布尔的灯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投下碎金,映得天花板微微发亮。风从没关严的窗缝钻入,带着咸味和远处清真寺晚祷的余音。
伊什塔尔把他扔在床上,动作不算轻,却也没让他撞到床头。
他的后脑磕在不太柔软的枕头上,发出一声闷响,大概是磕到床垫了。
他眉头微蹙,但没醒。
武道服领口被汗浸透,紧贴皮肤。她解开最上面两颗扣子,指尖擦过锁骨,烫得惊人。相反,她的掌心只觉温热,不再有那种从脊椎炸开的灼烧感。
他仰面躺着,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即便失去意识,身体仍维持着某种秩序,像一尊被雨水打湿却不肯倒下的石像。连昏迷都在守礼。
她坐在床沿,盯着他起伏的胸口。
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碰他时,身体会失控?又为什么,现在失控的变成了他?红子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俯身,靠近他颈侧。
呼吸滚烫,带着铁锈般的气息。
她轻轻嗅了嗅,没有香水,没有烟味,只有尘土,和一丝极淡的皂角香,干净得近乎固执。
她的唇贴上去时,他毫无反应。
她没动,只是停在那里,感受他唇瓣的温度。微凉,与滚烫的体温形成奇异的反差。
三秒,五秒。
直到他喉结无意识滚动了一下,像吞咽一个未出口的梦。
不再有那种几乎能摧毁意志的催情,她终于感受到了京极真身上源源不断的能量。
不同于其他人,她暂时感受不到他的能量究竟能干什么。
她轻轻咬住他的下唇。
他身下鼓鼓囊囊,又变硬了许多。像是难以忍受这种强烈的欲望,手指猛地攥紧床单,指节发白,小腿肌肉绷紧,却始终没睁开眼。
伊什塔尔的身子稍稍后退,看着他。
睫毛在眼下投出细密的阴影,额角汗珠滑落,没入鬓角。
这张脸在擂台上冷硬如刀,此刻却显出一种罕见的脆弱。
她脱掉衣服,到浴室冲了个澡,回来躺到他身边。手臂环住他腰侧,掌心贴上他汗湿的背。
肌肤相触的瞬间,一股温润的暖流再次覆上她的身体,而京极真的体温也在一点点下降。
她把脸埋进他颈窝,鼻尖蹭到他跳动的脉搏。起初急促,像擂鼓,之后渐渐平稳,像潮水退去。他的呼吸也从粗重变得深长,眉头舒展,仿佛终于卸下某种无形的重担。
她没说话,也没动,却在心里分析着这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
白马探能和她通过信物建立联系,京极真或许也可以通过这种奇特的方式和她建立联系。
不知过了多久,她也产生了困意。她抬起手,指尖描摹他下颌的线条。
硬朗,带茧,有一道浅浅的旧伤。
现在,他躺在她怀里,毫无防备。
她可以做任何事。
但她什么都没做。
赌盘开盘价一路飙升,因为决赛对阵表上那两个名字。
天城黎音(摩纳哥) vs 京极真(日本)
没人料到潘克拉辛能走到这一步。
伊什塔尔站在选手通道阴影里,指尖抚过颈侧。只是一晚,昨夜匕首擦过的伤痕就只剩下了浅浅白痕。
她吞下最后一口红子给的魔药,苦涩中带着一丝玫瑰的香气。
“十二小时内不会失控。”红子当时说,“但别指望它让你变成石头。”
她深吸一口气,走向擂台。
京极真正站在中央,白色武道服一尘不染,双脚微开,重心沉于丹田,双手自然垂落,是标准的极真空手道“自然体”起式。他没看观众,也没看裁判,目光只落在她脚步落点上。
裁判示意开始。
伊什塔尔没有废话。
她左脚蹬地,整个人如箭突进,右腿低扫直取他支撑腿膝窝。这是潘克拉辛最凶的开场,意在破坏平衡,继而抱腿摔投。
但京极真没后退。他左脚内扣,小腿肌肉绷紧如铁,硬生生扛下这一扫。
下一秒,他右拳如炮弹轰出。直线正拳,极真空手道的标志性技法,快得几乎撕裂空气。
伊什塔尔偏头避过,拳风擦过耳际,带起一阵刺痛。
她顺势切入内围,左手擒他右腕,右手锁他肘关节,欲借力掀翻。可京极真猛地沉肩,肘部如钢柱般纹丝不动。
他左腿闪电般踢出。中段前踢,直奔她肋下。
她松手后撤,却仍被踢中腰侧,闷哼一声。
掌心无意擦过他小臂。刹那间,一股热流从脊椎窜上后颈。
心跳骤快,指尖发麻。
但她咬住舌尖,压下那阵灼烧感。
魔药生效了,燥热被一层薄纱隔住,不至于失控。
确定魔药的效力,她不再追求一击必杀,改用游走战术,利用潘克拉辛的灵活性绕场周旋。
突然,她假意左扑,诱他出拳。
京极真果然右拳递出。
她瞬间变向,从他右侧切入,右膝猛撞其腰腹。
他闷哼,却未弯腰。
极真空手道讲究“受击如山”,越是痛,越要稳。
他左手抓住她衣襟,不是摔,而是猛地一拉,同时右腿横扫。
回旋踢!
风声呼啸,若被踢实,肋骨必断。
看来京极真确实认真起来了。
伊什塔尔仰身后折,脊背几乎贴地,发丝被踢风削断几缕。
起身瞬间,她欺身而上,双臂锁他咽喉。
全场哗然。
京极真脖颈青筋暴起,呼吸受阻,却未慌乱。
他双手并未去掰她手臂,而是猛地屈膝上顶,让伊什塔尔被迫松手后跳。
两人喘息交错,汗珠从额角滑落,在地板上砸出深色圆点。
节奏更快了。
她连续三次低扫,逼他不断格挡。然后,她虚晃一腿,突然跃起,右腿如鞭抽向他头部。
京极真抬臂格挡,小臂与她小腿相撞,发出沉闷声响。
两人同时后退半步,手臂都在颤抖。
又一次缠斗中,她的掌心按上他胸口,借力翻身。
热流再度涌上,但这次,她竟察觉到一丝异样。
他的皮肤在发烫。不是因为运动的热,而是像她之前那样,烫得不正常。
她心头一震,动作微滞。
京极真立刻抓住这半秒破绽,左脚踏前,右腿如刀劈下。
极真空手道最强杀招,力量集中于脚,若是用力大些,甚至可碎砖裂石。
她交叉格挡,却被踹得连退五步,肩胛撞上擂台边缘绳索,剧痛钻心。
但她依旧没倒。
咬牙站稳,摆出潘克拉辛的“战龟式”。重心下沉,双臂护肋,只露双眼。
京极真没追击。他站在原地,微微喘息,额角汗珠滚落。他的目光第一次有了波动,是终于遇到对手的热切。
两人再次对冲。
伊什塔尔佯攻左路,实则右腿扫下盘。京极真跃起避让,落地瞬间,左拳直刺她面门。
她偏头,右手擒他手腕,左手锁肘,欲使“海蛇绞”。但就在她贴近的刹那,掌心贴上他汗湿的胸膛。
这一次,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燥热竟然减弱了不少。而京极真却明显一僵,呼吸乱了一拍。
就是现在!
她发力拧转。可京极真竟在失衡瞬间,以不可思议的腰力强行稳住,反手抓住她衣领,借她自身冲势,将她狠狠掼向地面。
不是摔投,是投技中的崩落。极真空手道极少用,但一旦用出,便是终结。
她后背砸地,眼前一黑。
裁判立刻介入。
“胜者——京极真!”
掌声雷动。
伊什塔尔躺在地上,盯着天花板,胸口剧烈起伏。
右手微微发颤,不是因为痛,而是因差那半秒。
如果她再快一点,如果他没在最后关头稳住……
京极真走过来,身上也终于多了不少灰尘和破损递。
“你很强。”他说,“下次,你在第三回合换重心的时候,左膝比右肩更先暴露。你的小习惯在武道场上也会成为破绽。”
说完,他转身离开。
伊什塔尔爬起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只有像他这样观察细致,有足够经验,又真正算得上有天赋的武道巅峰级的选手才会真正抓住她的那一点破绽。如果换一个人,就算是发现了她的破绽,也不会那么轻易让她的‘破绽’成为破绽。
但他指出了她的破绽,这是武者的最高敬意,她收下了。
她摸了摸自己胸口,那里不再灼热,不同于之前,现在一点多余的感觉都没有。她想起他最后那一瞬的僵硬。
他的体温,好像……又升高了?
黄昏,场馆人潮退去。
伊什塔尔没回酒店。她坐在空荡的观众席最后一排,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右肩。虽然她在当隐形人的那些年里早就变得不怕死不怕痛,但京极真侧踹的位置的钝痛感还是让她感觉有些不适,能感觉到他当时到底有多用力。
虽然有些不甘心没有拿到冠军,但更让她感兴趣的是他最后那一瞬间的僵硬。是真的失衡,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风从高窗灌入,带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咸味。她忽然站起身,走向选手通道。
休息区早已清空。京极真的储物柜开着,里面只剩一条用过的毛巾。他的东西应该已经被教练或是同行人带走了,这条毛巾大概是他还没准备离开的时候放在这的。
总不可能是忘记了吧?
她伸手碰了下,布料冰凉,至少一小时前就离开了。
她走出场馆后门,沿着围墙缓步。
武道大会结束后,安保松懈,连便衣都撤了大半。只有清洁工在冲洗擂台血迹。
她本来应该回酒店的,可脚步却转向西侧。
那是他赛后离场的方向。
小巷幽深,堆着废弃的器材箱和折迭椅。她走过一半,忽然停住。
地上有一道拖痕,是身体被拖行时留下的压痕,从巷口延伸至一堆防水布后。
她蹲下,指尖沾了点灰,捻开,上面混着汗渍和一点暗红。
是血?还是擦伤?
她掀开防水布。
京极真正靠墙坐着,头垂在胸前,武道服领口敞开,脸上的红晕透过小麦色的皮肤也能看得十分清晰。他呼吸急促,额角全是冷汗,锁骨处皮肤泛着不正常的潮红。
她蹲下,试探他颈侧脉搏。
又快又乱。
“京极?”她轻唤。
没反应。
她伸手扶他肩膀,想拉他起来。但就在掌心贴上他皮肤的瞬间,那熟悉的燥热感涌上来。
奇怪的是,这次她只觉微温,像夏日余晖的温暖。而他的体温却烫得惊人,仿佛体内烧着一把火。
看来是症状转移了。
她立刻拨通红子的电话。
“喂?”红子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背景有烛火噼啪声。
“我碰到京极真了。”伊什塔尔说,“他晕倒了,体温异常高,但我几乎没感觉。”
电话那头静了一秒。
“哦?”红子轻笑,“看来药起作用了。”
“你的魔药做了什么,居然还有这种妙用。早知道我早用了,也省得我每次碰到他都受这种折磨。”
“不是‘做了什么’,”她慢悠悠地说,“是‘转移了什么’。那东西需要容器,你只是暂时保管。现在它找到更合适的了。”
“另外,我要提醒你一点。你之前遇到他的时候,我好像和你也没那么熟。”
别说熟了,她们甚至不认识。
伊什塔尔感觉有点有趣,但还是继续问她,“更合适是什么意思?”
“他的身体比你更能承受那种热度。”红子顿了顿,声音忽然压低,“红魔女的魔法,从来不会无缘无故选中两个人。”
“所以?”她问。
“所以——”红子拖长音,带着一丝戏谑,“既然他现在动不了……你不好奇,他心跳加速,到底是因为武道,还是别的?”
没等回答,她就挂了。
不是,她这话是何意味?
咬了咬牙,把脑子里的东西都清空,她俯身将他一只手臂搭上自己肩头,另一手托住他腰背,慢慢架起。
他比看起来更重,肌肉紧绷,即便昏迷也不肯彻底放松。
她咬牙撑住,一步步往酒店方向走。
路灯亮起时,她后背已湿透,但胸口不再发烫,反而有种奇异的平静。
回到酒店,她只开了一盏床头灯,暖橙色的光映得房间好像都温馨起来。
窗外伊斯坦布尔的灯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投下碎金,映得天花板微微发亮。风从没关严的窗缝钻入,带着咸味和远处清真寺晚祷的余音。
伊什塔尔把他扔在床上,动作不算轻,却也没让他撞到床头。
他的后脑磕在不太柔软的枕头上,发出一声闷响,大概是磕到床垫了。
他眉头微蹙,但没醒。
武道服领口被汗浸透,紧贴皮肤。她解开最上面两颗扣子,指尖擦过锁骨,烫得惊人。相反,她的掌心只觉温热,不再有那种从脊椎炸开的灼烧感。
他仰面躺着,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即便失去意识,身体仍维持着某种秩序,像一尊被雨水打湿却不肯倒下的石像。连昏迷都在守礼。
她坐在床沿,盯着他起伏的胸口。
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碰他时,身体会失控?又为什么,现在失控的变成了他?红子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俯身,靠近他颈侧。
呼吸滚烫,带着铁锈般的气息。
她轻轻嗅了嗅,没有香水,没有烟味,只有尘土,和一丝极淡的皂角香,干净得近乎固执。
她的唇贴上去时,他毫无反应。
她没动,只是停在那里,感受他唇瓣的温度。微凉,与滚烫的体温形成奇异的反差。
三秒,五秒。
直到他喉结无意识滚动了一下,像吞咽一个未出口的梦。
不再有那种几乎能摧毁意志的催情,她终于感受到了京极真身上源源不断的能量。
不同于其他人,她暂时感受不到他的能量究竟能干什么。
她轻轻咬住他的下唇。
他身下鼓鼓囊囊,又变硬了许多。像是难以忍受这种强烈的欲望,手指猛地攥紧床单,指节发白,小腿肌肉绷紧,却始终没睁开眼。
伊什塔尔的身子稍稍后退,看着他。
睫毛在眼下投出细密的阴影,额角汗珠滑落,没入鬓角。
这张脸在擂台上冷硬如刀,此刻却显出一种罕见的脆弱。
她脱掉衣服,到浴室冲了个澡,回来躺到他身边。手臂环住他腰侧,掌心贴上他汗湿的背。
肌肤相触的瞬间,一股温润的暖流再次覆上她的身体,而京极真的体温也在一点点下降。
她把脸埋进他颈窝,鼻尖蹭到他跳动的脉搏。起初急促,像擂鼓,之后渐渐平稳,像潮水退去。他的呼吸也从粗重变得深长,眉头舒展,仿佛终于卸下某种无形的重担。
她没说话,也没动,却在心里分析着这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
白马探能和她通过信物建立联系,京极真或许也可以通过这种奇特的方式和她建立联系。
不知过了多久,她也产生了困意。她抬起手,指尖描摹他下颌的线条。
硬朗,带茧,有一道浅浅的旧伤。
现在,他躺在她怀里,毫无防备。
她可以做任何事。
但她什么都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