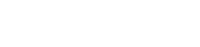元舒感到顿痛,不只因为五指传来的触感,还有头顶恶狠狠的语气,还有带着怒气却冷漠无比的眼睛。
这一切让她抽气都困难起来。
好像自己真的做错了。
好像这个人对自己厌恶极了。
就算自己对于她什么也不是,可是元舒还是没办法不感到伤心。
指针转动,元舒还留在冰凉的地板上,唯一的不同就是她的脚腕与床尾之间多了一条挣不开的链子。
被束缚的过程中元舒不是没有想开口解释,或是道歉,或是软着模样讨好她,可是江尧没再正眼看她一秒,元舒无法在如此低的气压中为自己狡辩,甚至连呼吸都困难。
“假我给你请了,我要下楼买点东西准备晚饭,如果累了,你可以到床边坐着。”
“我回来之前你就在这里认真反思。”
“如果因为乱动又弄伤了手腕可没人管你。”
她走之前是这么说的,然后门板转动,把最后一点暖光隔绝在外。
……
临近冬天,天色暗的快,不知道眨了多少次眼睛,屋内的家具全都模糊起来,尤其在蒙着泪光的昏沉光线里,忽远忽近。
要反思什么呢?元舒不清楚也不明白,又或者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必须要承认的。
这些事在自己眼里只不过是顺理成章,生活上的一点小磕碰而已,元舒懂得知足常乐,这样的日子已经算得上安逸了。毕竟自己不求什么,也不配什么,如果硬给她什么好东西,或许也会变成一种怪异的负担。
但话说回来,其实根本不需要反思自己也能对着江尧说出对不起,因为元舒的一次次道歉不为别的,就是对不起自己,一次次惹的江尧着急,生气,疲惫,麻烦……
迷迷糊糊闭上了眼,只一会儿又醒过来,元舒感到有些口渴。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撑着僵硬的身子起来,眼前一阵天旋地转的晕眩,大腿抵在了床边,然后顺势坐了下去,这是距离拴着自己最近的那一角区域。
桌子在那一头,元舒仅仅几步就走到自己活动范围的极限,只要再伸伸手就能触碰到杯壁了,可唯一管用的手好像在刚才就如江尧诅咒一般的话出了问题,失控一般不知轻重的将杯子拨弄到地上。
啪——
随着裂痕争先恐后的迸发出逃的水液,又抵抗不过引力重重砸在地面,仅余的最后一点力气冲远了玻璃碎片。
元舒愣了几秒,不知道是不是被尖锐的破碎声扎到了耳朵,忽然不顾脚下的碎片蹲下来胡乱摸着地面,嘴里小声嘟囔着什么。
“我能收拾干净……不是故意的、”元舒开始自顾自的念叨,尽管这家里除了她空无一人。
好像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不管是谁摔碎了东西,都是一件很让人恐惧的灾难。
多处的刺痛稍微让她清醒了点,怎么清理也还是能摸到混着玻璃碴子的水液,就连右手的纱布也染了血色。
此刻身心俱疲。
元舒想起来了,江尧说,累了可以坐在床边,她现在觉得很累,很累。
可坐在床上又如坐针毡,惹了祸还能心安理得的坐在床上吗?
要是被江尧发现怎么办,洒的是水,却犹如火上浇油。
想到这元舒赶紧从床上下来,又窝回床尾的那处地板,是她一开始被安置的地方。
在这之前也不忘记把方才坐过的床单褶皱抚平。
……
这一切让她抽气都困难起来。
好像自己真的做错了。
好像这个人对自己厌恶极了。
就算自己对于她什么也不是,可是元舒还是没办法不感到伤心。
指针转动,元舒还留在冰凉的地板上,唯一的不同就是她的脚腕与床尾之间多了一条挣不开的链子。
被束缚的过程中元舒不是没有想开口解释,或是道歉,或是软着模样讨好她,可是江尧没再正眼看她一秒,元舒无法在如此低的气压中为自己狡辩,甚至连呼吸都困难。
“假我给你请了,我要下楼买点东西准备晚饭,如果累了,你可以到床边坐着。”
“我回来之前你就在这里认真反思。”
“如果因为乱动又弄伤了手腕可没人管你。”
她走之前是这么说的,然后门板转动,把最后一点暖光隔绝在外。
……
临近冬天,天色暗的快,不知道眨了多少次眼睛,屋内的家具全都模糊起来,尤其在蒙着泪光的昏沉光线里,忽远忽近。
要反思什么呢?元舒不清楚也不明白,又或者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必须要承认的。
这些事在自己眼里只不过是顺理成章,生活上的一点小磕碰而已,元舒懂得知足常乐,这样的日子已经算得上安逸了。毕竟自己不求什么,也不配什么,如果硬给她什么好东西,或许也会变成一种怪异的负担。
但话说回来,其实根本不需要反思自己也能对着江尧说出对不起,因为元舒的一次次道歉不为别的,就是对不起自己,一次次惹的江尧着急,生气,疲惫,麻烦……
迷迷糊糊闭上了眼,只一会儿又醒过来,元舒感到有些口渴。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撑着僵硬的身子起来,眼前一阵天旋地转的晕眩,大腿抵在了床边,然后顺势坐了下去,这是距离拴着自己最近的那一角区域。
桌子在那一头,元舒仅仅几步就走到自己活动范围的极限,只要再伸伸手就能触碰到杯壁了,可唯一管用的手好像在刚才就如江尧诅咒一般的话出了问题,失控一般不知轻重的将杯子拨弄到地上。
啪——
随着裂痕争先恐后的迸发出逃的水液,又抵抗不过引力重重砸在地面,仅余的最后一点力气冲远了玻璃碎片。
元舒愣了几秒,不知道是不是被尖锐的破碎声扎到了耳朵,忽然不顾脚下的碎片蹲下来胡乱摸着地面,嘴里小声嘟囔着什么。
“我能收拾干净……不是故意的、”元舒开始自顾自的念叨,尽管这家里除了她空无一人。
好像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不管是谁摔碎了东西,都是一件很让人恐惧的灾难。
多处的刺痛稍微让她清醒了点,怎么清理也还是能摸到混着玻璃碴子的水液,就连右手的纱布也染了血色。
此刻身心俱疲。
元舒想起来了,江尧说,累了可以坐在床边,她现在觉得很累,很累。
可坐在床上又如坐针毡,惹了祸还能心安理得的坐在床上吗?
要是被江尧发现怎么办,洒的是水,却犹如火上浇油。
想到这元舒赶紧从床上下来,又窝回床尾的那处地板,是她一开始被安置的地方。
在这之前也不忘记把方才坐过的床单褶皱抚平。
……